采访媒体:时尚健康 周鑫、贺梓秋、Tina
采访对象:绿色和平 刘君言
以下采访内容来自可持续发展经济学博士、国际环保组织绿色和平(Green Peace)东亚分部“气候风险项目”负责人刘君言,首发自《时尚健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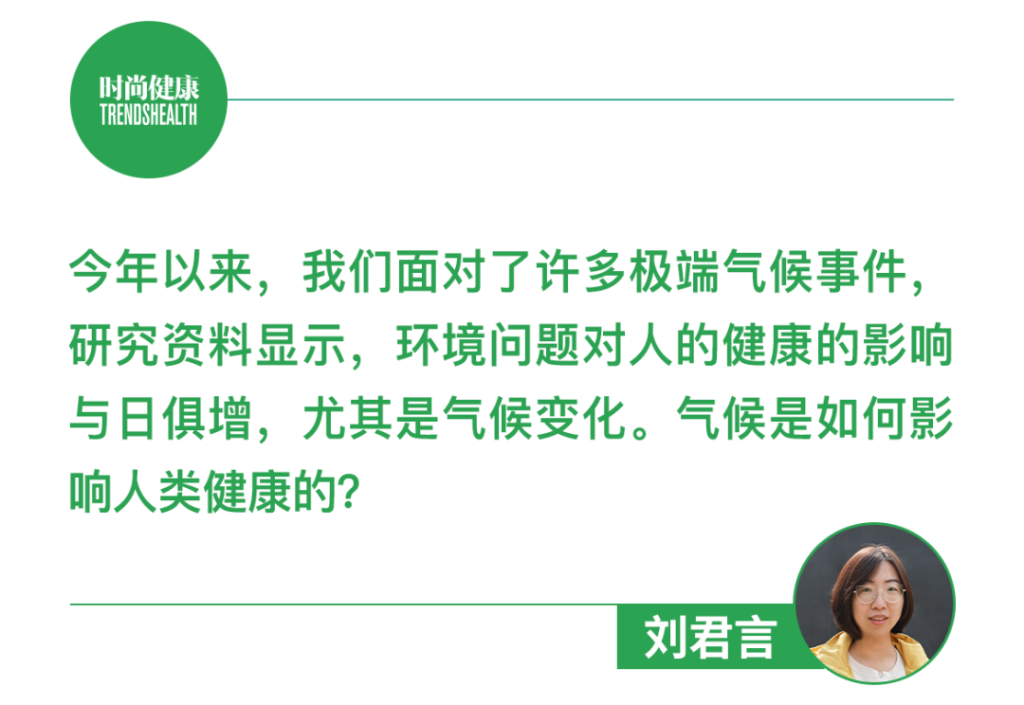
气候的变化会加剧传染病、过敏症等一类病症,最近国内冬季寒潮来临,气温骤降,对心脑血管、呼吸系统等都有显著的影响。
气候变化对健康的影响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气温变化所带来的健康风险。
举个最直接的例子,2021年我们和国家气候中心的专家合作研究并撰写了《中国主要城市区域气候变化风险评估及未来情景预测》报告,关于中国主要城市区域的气温风险的评估,报告中特别关注的就是极端高温热浪和极端暴雨这两类事件。
我们注意到比如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这样的城市区域,气候变化所带来的极端事件的频次和强度不断增加。再比如杭州,60年以来,杭州地区出现过429次高温,2000年后就占到了41%,即170多次。
另外一方面是湿度带来的变化,以北京为例,北京的热一般是干燥的热,但是近些年湿度也在不断增加,这种高温叠加高湿的情况,就会使得热射病发病几率快速上涨。而高温热射病对某些人群有格外显著的影响,一类是户外工作者,2023年北京有一位导游因为高温热射病离世。
另外还有很多虽然没有发生死亡事件,但是实际工作需要长期暴露在高温环境下,诸如建筑工人、快递员、外卖员等职业;还有一类是生活在北京胡同区域的老年人,胡同里的房子虽然层高比较高,相对来说会比较阴凉,但现在胡同里有很多棚户建筑类的非正式住宅,这些住宅不仅室内高温而且降温措施很少,热射病发病的几率很大。对于本身对高温天气不是那么敏感的老年人来说,热射病是非常危险的事情。
在气候变化下,气温波动的波峰和波谷都在提高,波峰是高温热浪,波谷是极端寒潮,寒潮对心脑血管疾病的影响更为显著。急剧的温差变化影响血管的收缩,有基础疾病的老年人对这种巨大温差变化的适应能力很差,患病的风险也就更高。
同时,一些传染性疾病也在增加,比如很多虫媒传染病,最典型的就是登革热。1970年代,全球登革热仅集中于一些区域,但是现在由于全球平均温度的变化,虫媒传染病的传播媒介,比如蚊虫等,有了更广阔的活动区域,活动的时间也会更长,这就导致了登革热传染的范围变得更广、影响更大。
这两类健康风险是我们在气候领域尤为关注的,更不用说灾害性事件。我们常听一句话叫“大灾之后必有大疫”,暴雨、洪涝之后,都会导致一些列的环境污染和疫病蔓延。气候变化风险最大的一个特征就是复合性,不仅仅是单一的灾害,而是会和其他一系列的环节结合起来,形成一个复合性的风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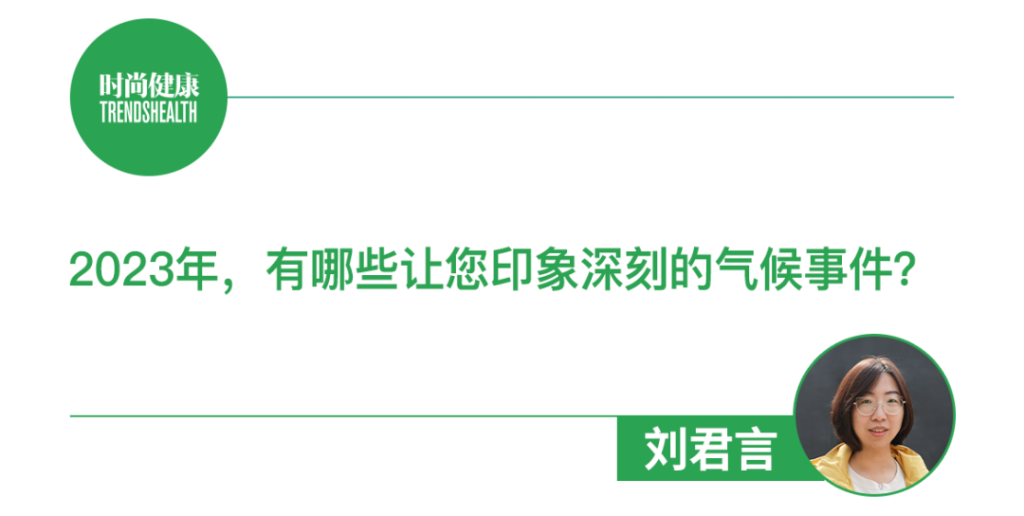
2023年印象特别深刻的,一是4月份北京的沙尘暴,北京已经很多年没有经历过这么严重的沙尘暴了。
那段时间我们在甘肃做一个关于“气候变化对西北的区域的影响”的项目,我们到达民勤县的第一感受就是“震撼”。民勤位于腾格里和巴丹吉林沙漠中间的一片绿洲上,那边花了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资源去做防沙治沙,让日渐消失的绿洲重新恢复,在国内是很有标志性的。我们和当地的气象以及林草部门人员沟通的时候,了解到近些年以来防沙治沙的工作尤为艰难。
首先,防沙治沙工程只是去控制一部分地表的沙源,近几年随着温度上升,蒸发量也随之增加,使得这里更加干旱。别的地方的梭梭树可以活50年,但民勤的梭梭只能活20年不到,种一批死一批的情况也很常见,这说明光靠防沙制沙工程去彻底消灭沙尘暴是十分不现实的。
以蒙古国为例,这几年春季外蒙的沙源地的影响特别大,一方面是因为由于工业产业的开发导致植被生态被破坏,生态系统快速退化;另一方面是由于春季的干旱,春季比预期来得更早,但地表的植被还没有完全生长出来,春季回暖带来的大风就会将尘土扬到高空之中再传输过来,沙尘暴也就在我国北方地区不断增加。
张掖市高台县祁连酒厂葡萄种植园,村民在为春季葡萄萌发做准备工作。气候变化还对河西走廊的酿酒葡萄种植业造成影响,春季的晚霜冻会让刚刚萌发的葡萄新芽冻伤,严重影响葡萄产量。
还有今年的高温,6月22日那天,北京南郊观象台气温飙升至41.1℃,是有观测记录以来历史第二高。而且不光温度高,湿度也高。这种高温叠加高湿的环境特别危险,高温健康风险的指数其实不仅仅要看温度,更要看湿度,每增加10%,危险系数会呈指数型的增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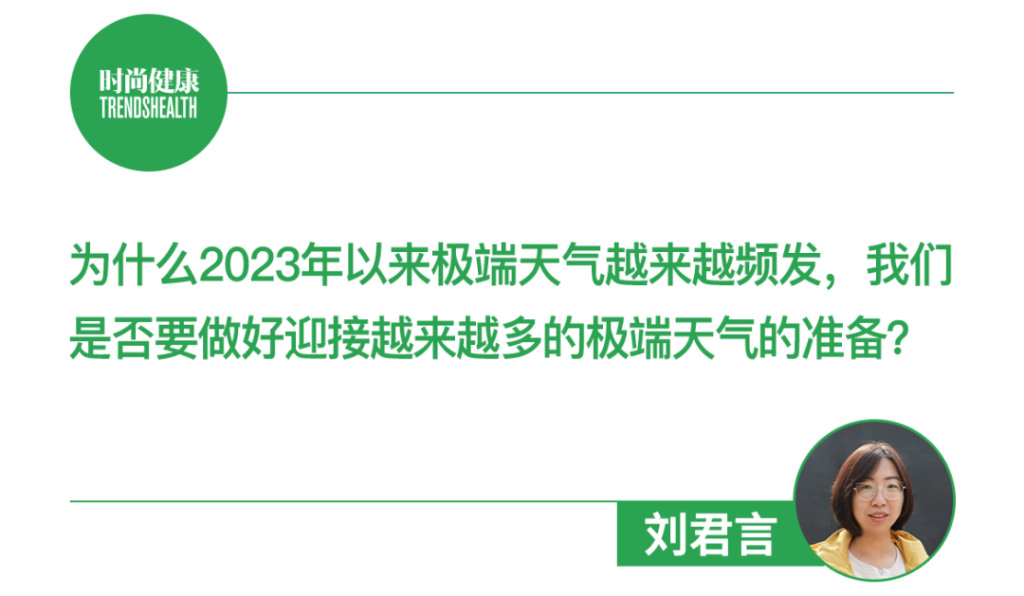
首先我们先理解“极端”这个概念,在气象方面,包括气象局气候中心会有一套根据历年数据形成的标准体系去判断什么是极端。纵观过去六十年,极端天气出现的概率很低,基本低于5%-10%。
但现在我们会发现这些“百年难得一遇”的极端情况出现得越来越频繁,这是因为我们现有的标准其实已经跟不上目前气候变化的趋势了。
特别是在2000年这个拐点之后,极端气象气候事件的发生频次快速增长。未来的气候还会变得多极端?频次和强度变得有多快?我们现在这种线性推演的方法很难推算出准确的结果。
举个例子,2021年,我们在做城市群气候风险报告的时候,珠三角和长三角我们都做了极端暴雨的数据预测,但是京津冀的做不出来,近60年来,京津冀极端暴雨的频次并不高,所以我们无法获得准确的数据,结果2023年就来了一次极端暴雨。
2021年,我们发布的《与“洪”共存——中国主要城市区域气候变化风险评估及未来情景预测》报告有很多讨论,一些人觉得报告内容太过悲观,明明已经提倡了积极面对,为何还要“与洪共存”呢?但这是必须要面对的现实——我们要与洪水共存很久。
我们目前的一个大缺口,就是我们该如何更好地为未来的灾害做好准备。2023年洪涝灾害之所以在北方受到特别关注,就是因为北方面对洪涝灾害的基础设施和应对能力没有做好应灾准备。
我们对气候变化有特别多的未知,尤其是它的危险性。我们知道它会快速发展,也知道它会呈指数性增长,但是我们对很难预测到未来极端事件会在哪里何时发生,大家的应灾能力也相对薄弱,基础设施也还未做好准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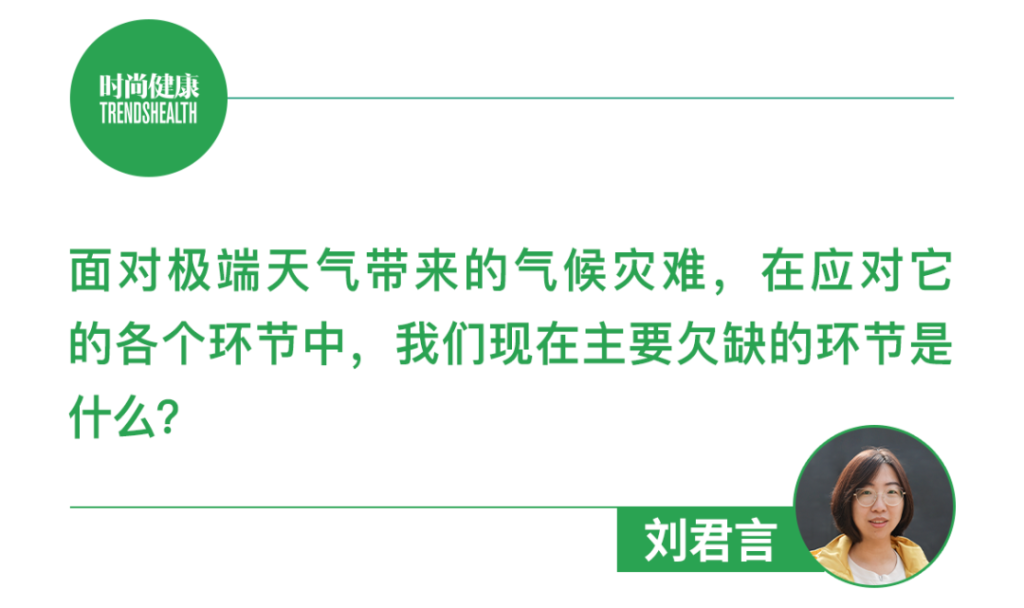
关于气候变化的应对,可以注意到无论是主流媒体还是社交媒体的叙事,都集中在两点:一个是强调政府和政策的作用,另一个强调的是个人,比如倡导节能减排、绿色生活等。但是国家和个人之间留下了一片巨大的空白,这个时候就需要社区来填补。
社区是我们聚集生活的一个区域,也是我们精神和生活上所依赖的一个区域。城市的更新需要时间,但灾害随时可能发生,这中间就需要社区发生作用。社区的参与和响应对于灾害的应对尤为重要。不同地区面对不同的灾种都有不同的响应方式和应对措施。
比如杭州在2017年的时候做了第一本社区气象灾害地图,邀请社区和本土的NGO组织合作,通过对致灾因子、社区脆弱性与暴露性这三个指标的分析,对于工程类和非工程类这两种防灾减灾能力的评估,做了一个灾害风险的分级。
但这个地图到目前为止也只在一个社区去做了试点,因为社区除了要做气象的灾害的评估之外,还要不断地更新地图,让居民在灾害来临时自己知道如何应对。还有广东也在做一个参与式和访谈式的社区灾害风险评估,来提高居民的应灾意识。
社区自身拥有一个自救互助的网络体系是更加关键的,在灾害来临的时候,能尽可能调动最大限度的人力和物力去挽救生命。
我们刚刚做的气候风险响应工作坊首先邀请了很多的社会组织和地方社会组织,比如绿色浙江、杭州市生态文化协会等一起加入进来研究风险气候、社区级别的风险评估和灾害应对该怎么做。
其次也邀请了很多做社区营造和基金会的伙伴加入我们,让社区进行改造加入气候的视角。而且基金会也给社区提供了一定的经费来帮助他们去做响应工作。但这一切还只是刚开始进行尝试,我们也不过是摸着石头过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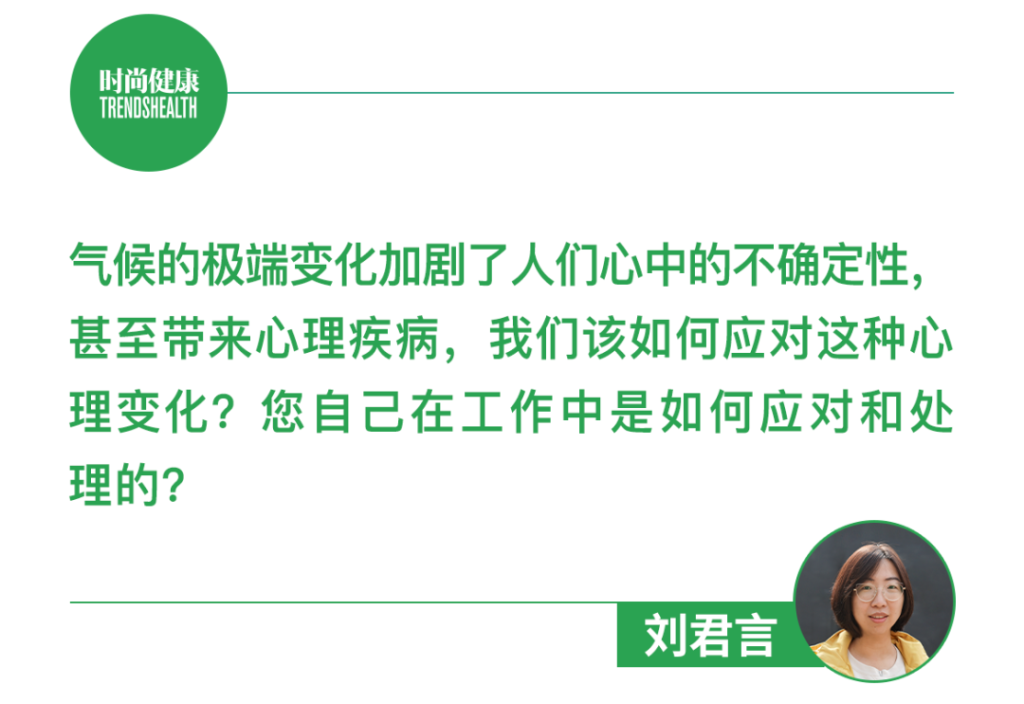
经过疫情这几年,大家心中对于未来,甚至当下都有很多不确定性,目前气候的变化更加加剧了大家心中的这种不确定性,我们将其称为气候变化抑郁症症候群。面对这样一个如同庞然大物的危机,对于我们能做什么这件事大家都会感到迷茫和无力。
从个体上来说是两重的“与我无关”:第一重“与我无关”,是我不知道这跟我有什么关系;第二重“与我无关”,是我不知道做什么可以有效地去应对它。这就是造成现在大部分人有气候变化抑郁症的一个典型过程。
所以对于我来说,我会想是什么让我继续从事这份工作?其实是看到更多伙伴的加入,参与到气候变化这样的公共议题中来,我也能从中获得能量和满足感。
我们有个同事2023年在京津冀暴雨的时候就哭了,因为河南暴雨的时候我们就提了很多关于应急响应机制的问题,从预警到应急响应有一个巨大的缺口,但是城市建设和应灾意识都没有跟上。2021年到现在,暴雨的悲剧再次重演。
但其中能给我们提供精神力量的就是很多在前线救援的这些行动者的故事,还有人冲在前面,我们就觉得,我们还可以再接着干下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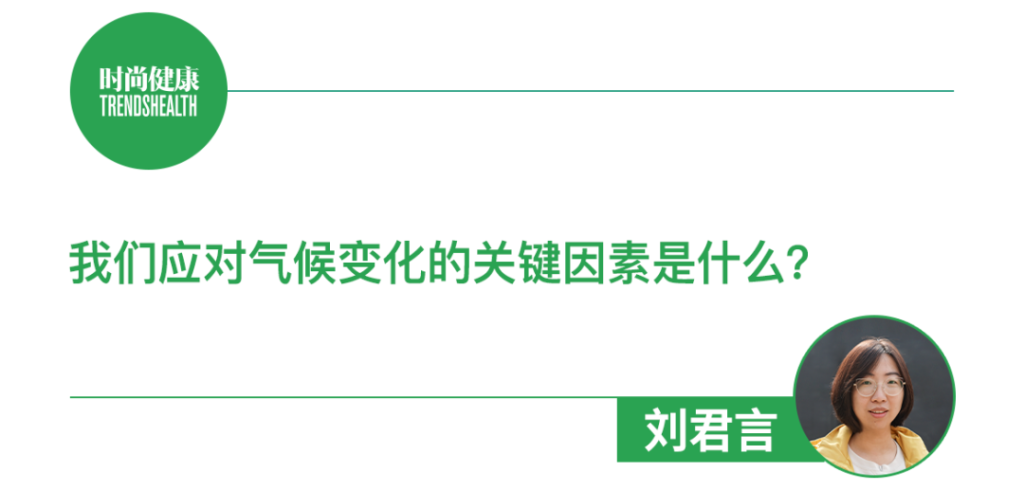
还是在于人本身。这也是我做气候风险项目的一个初衷——要把气候这个话题拉回到人本身。当我们讨论气候变化,要么在谈论绿色低碳发展、能源系统变革,要么在谈论气候变化在科学层面上的影响,但这两种叙事都不足以打动普通个体,很难让个体感受到自身行动的有效性。既然如此,那我们就把气候变化和人本身结合起来,重新去看它和人的关联在哪里。
人本身与气候变化的关联,和我们现在已有的社会经济结构、文化结构等息息相关。气候变化的议题永远不能脱离人本身去谈,一个人口如此庞大的国家的转向不能仅靠一辆马车去拉动,只能是集体的共同努力来推动。而很多人开始认识气候,其实是从日常生活的变化开始的,所以我们要从社区开始,从人的日常生活开始行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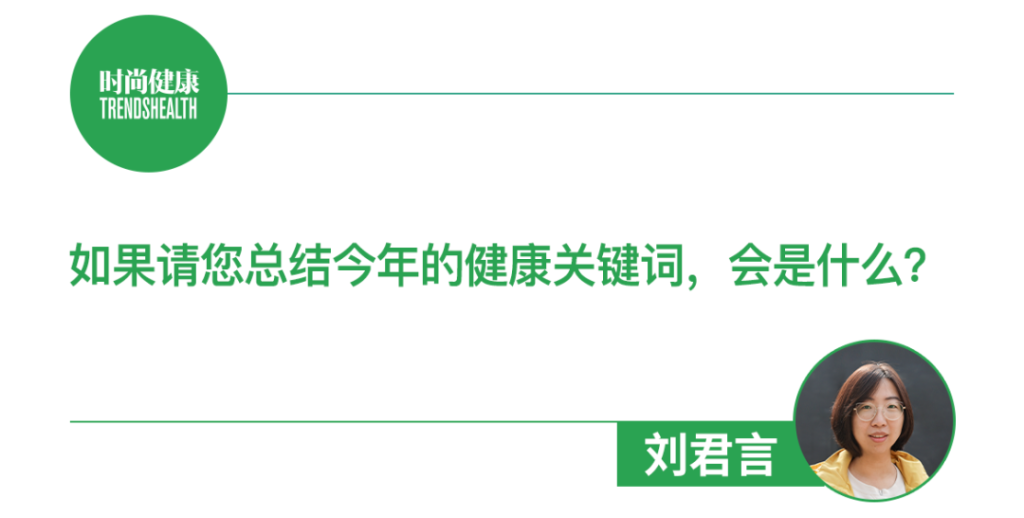
紧急/emergency:气候变化是一个巨大的公共卫生的危机,它是一个紧急状态,但是我们对稀有变化和健康的认知还很少。很少有人能将外部环境的变化联系到个人的健康,所以在应对突发事件时,就显得紧急。
脆弱:在健康和公共卫生领域的话,我们除了去关注它这种广泛的影响之外,我觉得我们还要额外的关切的就是这些脆弱人群,有可能他们会成为我们去应对危机的那块“木桶的短板”。





